“精英教育”如何影響階層流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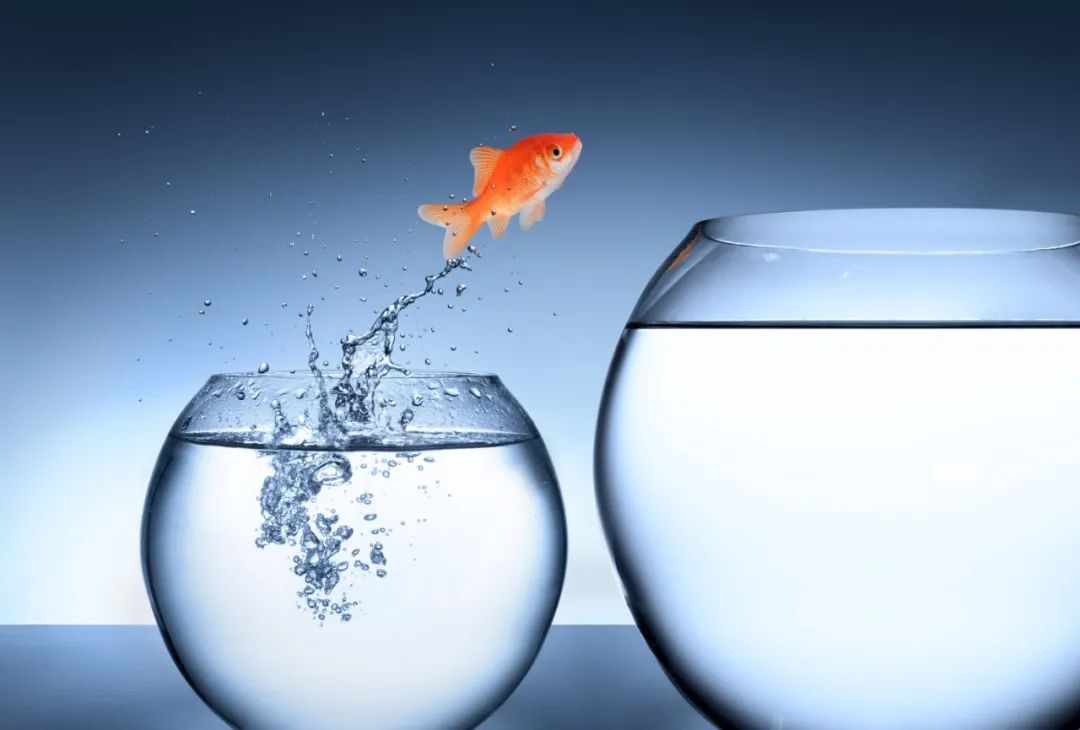
導語
當我們將成功視為多元的,就能看到其實有多種通往成功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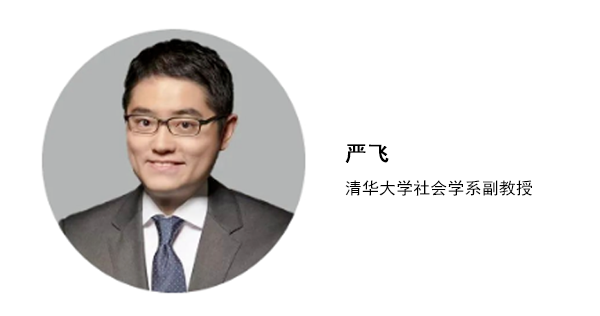
在知識分享社區“知乎”上有一條非常火爆的貼,叫做“上清北(清華大學或北京大學)真的可以改變一生嗎👯♂️?”這一話題在網絡上引起的熱烈討論👌,迄今已得到超過一萬多名網友的關註😲,累計瀏覽量超過了一千兩百萬🙂↔️。在該話題下的一千多個回答中,有的說所謂改變一生,上985和211名校可以⛹🏼♀️👮🏼♀️,上一本二本普通學校可以,上藍翔可以,甚至只是考上高中也可以🚵🏽♂️。
另一個可以關聯在一起的故事,是一項名為“青雲學子計劃”的教育實驗,從北京外來打工者的子女中選拔出了一部分最聰明的孩子🧑🏻🤝🧑🏻🩼,試圖將他們從嚴密殘酷的教育選拔中抽離,讓他們不從體製教育中滑落,最終能擺脫逾越階層、跨越界限。然而🧑💻,就像《人物》雜誌在《一群窮孩子的人生實驗》這一篇報道中所說的那樣:“這不是童話般的完美故事,過程坎坷動蕩💆🏿♀️,理想和復雜現實兼而有之。”升學製度🪅🍬、戶口政策🩺、原生家庭🤸🏽,這些問題接踵而至🤾👩🏽🔧。最終這個“天才班級”並沒有完成預期的目標,而其巨額的教育投資似乎也和最後的結果不成正比🙄。
盡管實現社會流動的機製有很多,但其中絕大部分都是外在於個人努力的(如父母人脈圈等社會資本)或具有偶然因素的👨🏿🚀。與這些機製相比,大學教育及其所帶來的文化資本在社會分層方面的穩定性和相對易獲得性優勢便得到了淋漓盡致的體現,成為了打破《管子》中“是故士之子恒為士🧄,農之子恒為農⚈,工之子恒為工,商之子恒為商”的精英再生產最重要的渠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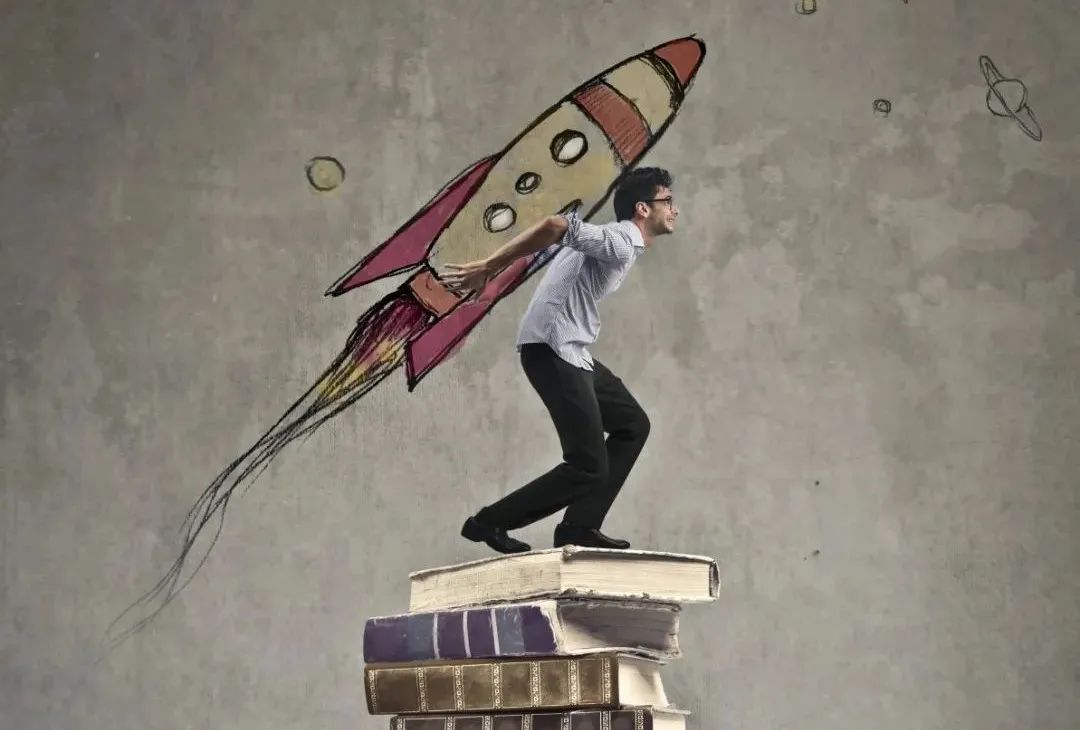
在學術界,多數學者都認同教育是劃分社會階層結構的重要依據和手段。例如,法國思想家布迪厄在《國家精英🕵️:名牌大學與群體精神》(The State Nobility: Elite Schools in the Field of Power)一書中就曾強調,“教育機構被資本和權力劃分為一個個場域……學習能力與文化資本♡、社會資本正相關”;美國公立學校之父賀拉斯·曼恩(Horace Mann)也曾提出,“教育超越人類其他任何方法,是人類環境偉大的平衡器🐦⬛,即社會機製的平衡之輪”的經典論述(參看巴蘭坦:《教育社會學》,江蘇教育出版社👩🦱,2005,第51頁),賦予了教育在社會系統中至高無上的地位。
從社會學的角度出發🤵🏼♀️,對於教育分層的研究👩🏽🚀,有著功能論與沖突論兩種基本的理論範式。功能論認為社會通過有效的機製,將其社會成員分配到不同的社會位置上以承擔相應的責任🤦🏽♀️,而學校則扮演著根據個人能力水平培養學生成為適應社會需要人才的角色,因此社會分層源於個人能力差異,學校因此成為了社會分層秩序的平衡器💁🏼♂️。而沖突論則對此提出反駁,強調社會分層的根源是社會階層之間的資源分配差異☝️🅰️,學校是各個階層之間競爭的戰場:精英階層試圖鞏固自己的支配地位🤷,而下層階級努力抗爭企圖擺脫被支配地位。由於“精英階層”最終擁有著學校教育的控製權,因此學校成為社會再生產的工具。
沖突論的解釋路徑又可以被分為結構性視角和能動性視角:前者更加強調社會結構和環境的製約作用🙆🏽♂️🪣,認為學校的社會階層結構對再生產的過程起到決定性作用;而後者認為個人和家庭在具體的社會情境中具有一定的主觀能動性,因此有超越社會階級結構限製的可能。結構視角的代表性理論是布迪厄的“文化再生產力理論”。在布迪厄看來🤏🏿,“精英階層”能夠通過文化資本和學校結構的巧妙結合實現社會再生產🍈,再輔之以必要的社會經濟資本🎅🏿,最終身體型文化資本轉化為製度型文化資本(教育文憑),進而轉化為經濟資本,由此再生產了資本分配不平等的社會結構。而能動性視角的代表性理論則有英國社會學家約翰·戈德索普(John H. Goldthorpe)等人提出的“理性選擇理論”。區別於強調不同階級的文化差異,這一理論更強調家庭與個人的理性選擇🤸🏿♂️,家庭對於教育的投入受到升學所需要的成本📬、未來能順利畢業的可能性🤜🏼、畢業所帶來的經濟和社會受益等因素的影響。然而,“精英階層”家庭在這幾種因素上相比於下層階級家庭具有絕對優勢,如教育的邊際成本相比於家庭經濟資本較低💆🏽♀️,文化資本決定著他們的子女更容易順利畢業而拿到文憑,“精英階級”的子女有更強的驅動力繼承父母的階級地位🧑🏿🦱❤️🔥。
從在校教育來看🦛,“精英高校”又是上層社會的縮影🧍🏻♀️。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社會學教授蘭德爾·柯林斯在《文憑社會》(The Credential Society)中就曾指出,學校不是獨立於權力和階級而存在的桃花源,也不是純粹為追求知識和真理而存在的象牙塔。如果忽視了教育系統中的文化生產過程與權力關系,就無法意識到它完全可能成為既得利益者維系特權和掩蓋社會不平等的工具💁🏻👩🏿⚕️。即使是最基本的學業學習也存在著隱形的機製和人際關系🧙🏿♀️,以及大學生活中種種隱晦的運作規則。《出身:不平等的選拔與精英的自我復製》(Pedigree: How Elite Students Get Elite Jobs)一書的作者勞拉·裏韋拉(Lauren A. Rivera)就揭露了名企選拔精英的邏輯👮♀️🧑🔧,看似公平的競爭實際上建構了不平等的選拔,成為精英自我復製的助推。在今天的中國⬜️,這種情況也日益普遍👨🏻🦯➡️⛓,頂尖企業的招聘官更看重契合、驅動力等主觀因素✋🏼,本質上是在挑選與自己和客戶更加合得來的“同類人”。
當然🤧,單從階層流動的角度考察優質高等教育的作用,結果不免悲觀🛣。社會學的研究世界中,喜歡用馬克思的“異化”和韋伯的“鐵籠”來描述我們當下的社會形態,似乎都在表明一種無奈而悲傷的傾向:人變得越來越像一個快樂的機器人,進而越來越成為更大的系統結構中的一顆小小的螺絲釘🙅🏻🔋。在知識性填鴨和學校社會功利性質的規訓之下🗾,我們會不斷拼命地追求分數,進而傾向於覺得高考即是人生的巔峰🧑🏿🎓,甚至掌握了未來人生的決定權。當我們接受了這種單一的價值觀🧚🏽♀️,就會對人生周期缺乏認識📭,只會將人生階段按照年齡和應達成什麽目的來劃分。
但另一方面🦵🏿,無論現代社會將人的生活怎樣理性化,把人的一舉一動都嵌入到宏觀機器之中🤥🙎🏼♂️,人的一生依然是“有機”的。進入大學和社會,可接觸到的資源以及需要面臨的選擇在數量和種類上都是指數級的增長,相比知識性的學習,更需要的是人的非知識性經驗和能力。在這個過程中,人格和情懷,判斷世界和思考問題能力的形成同樣十分重要👩🏻🎨。可以說👨🏻🎓,文憑決定的是社會經濟地位的下界,而視野格局👨🦯➡️、人生觀和價值觀是最終人生高度的關鍵因素。

或許我們真正應該考慮的是,教育的本質到底是什麽?當我們僅僅把教育視為對人進行分類和編碼的配置機製,並且和其作為提升社會地位的途徑掛鉤👩👧👧,我們已經是在利用一種冷酷和功利的角度去看待教育,教育也因此成功發生了異化🫛。這也源於社會對所謂的“成功”的單一和狹隘的標準🏃,即只有達到了足夠高的收入和社會經濟地位♗,才能被稱作“成功”人士3️⃣🦵🏿。教育的本質應該是讓所有人更加了解自己並最大限度發揮自己的優勢,真正掌握自己的人生而不是任由其他因素擺布。當我們將成功視為多元的,就能看到其實有多種通往成功的道路。英國教育理論家艾爾弗雷德•懷特海(Alfred Whitehead)在《教育的目的》(The Aims of Education)一書中曾說👳🏿♂️,“教育的問題是如何讓學生借助於樹木來認識樹林……教育只有一個主題那就是多姿多彩的生活”🏊🏼。因此🙎🏽,教育應該使人學會認識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方法論,習得他所在共同體中被廣泛贊譽的美好的道德情操,在廣闊天地中無拘無束地探索,尋找人生的方向。
如果我們從這個更廣泛的意義上理解教育的含義📓,那麽“青雲學子計劃”的結果便不是失敗的。就像一位計劃的受惠者說的🧮:“我覺得它是成功的,它教會了我們,如何做一個向上的人、一個正直的人。”因此🧗🏼,盡管人生的改變有太多的基礎決定因素和外界幹擾,但我們要做的是盡可能地拓展自己人生的廣度和寬度,形成獨立思考的批判精神和不斷追求進步的積極心態,從而創造出獨特的人生價值。
*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編輯:潘琦。